◎ 葛 鑫
蝉,又叫知了,是夏日的一道风景。
我在江南居住的小区绿化甚好。小区两面环河,河边一排茂密的树林。每逢夏日,树林里便会响起嘹亮的蝉鸣。傍黑的时候,偶见有孩子拿着手电筒照知了的幼虫——知了龟。
这让我想起千里之外的山东老家。儿时的记忆里,夏天,怎么能离得了知了呢,无论知了还是知了龟,无不充盈着我的生活,让我的童年生动而美好。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,父亲被调去了三十里外的乡村中学。夏天,每逢周末,父亲都会给我们带回来一些知了龟,那是他晚上抽空摸的。在父亲的描述中,校园里那片有许多知了龟的树林是那么神秘、美好。因为工作忙且不好存放,父亲每次带回的知了龟并不多,有时十几只,有时二十几只,但这些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,却足以让我们兴奋。母亲一般会给我们油煎了吃。油煎后的知了龟,色泽金黄,外酥里嫩,干香味美,吃起来十分满足。而父母却不舍得吃,总会留给我们兄妹打牙祭。那时的每个周末,我们都盼着父亲带着知了龟回来,直到秋天没了蝉鸣,我们依然盼着。
后来,我们搬去了父亲工作的学校居住,终于看到了父亲口中的那片树林。树林沿着校园的围墙,有很大一片。
夏日的树林,树木苍翠茂密,蝉鸣阵阵。“蝉噪林逾静”,幽静的树林里,时常会有学生在树荫下读书,偶尔还会跑过一两只野兔。傍晚,太阳刚落山,便有孩子拿了手电筒去树林里摸知了龟。如果天还没黑透,孩子们便会拿根树枝,去地下寻找知了龟的洞穴,特别是下过雨后的黄昏,收获最大。知了龟生活在地下,前面长有一对强壮的开掘足,土将军一般。我和哥哥最乐此不疲的便是去抓这些“土将军”。当我们寻见小洞,若稍微一挖,小洞骤然变大,那么,接着展现在眼前的十有八九便是知了龟的大前足了,我们便趁势捉去。每当捉到一只,我们便兴奋地喊一声,其间的欣喜可想而知。天渐渐黑下去后,我和哥哥便在树林里用手电筒挨棵树上照,然后用手去摸,每晚总能摸到十来只。但听说树林原本是坟地,我们人小胆儿不大,每次都早早收了场回家去了。而父母每晚忙完自己的工作后,都会到树林里去照照、摸摸,每次都不会空手。我们第二天早晨醒来,通常会在脸盆里看到簇拥在一起的二三十只知了龟,有的慵懒蜷缩,有的已经蜕皮羽化。若碰到蝉正开始蜕皮,我们就蹲在那里看着。小知了都是头先出来,紧接着露出绿色的身体和褶皱的翅膀,待到身子全出来后,它便静静地趴在那里不动了,一直等到翅膀变硬,颜色变深。当然,更多的时候,母亲会倒些水在里面,知了龟便不会那么快蜕皮了。
到了暑假,蝉鸣更加响亮。正午,我便跟着哥哥去粘知了。我们扛着早准备好的长竹竿,一颠一颤地到树林里去寻找猎物。学生放假了,父母在午睡,整个校园都看不见人,每棵大树梢上都传来蝉鸣。知了喜高,大部分竹竿都够不着,偶尔发现一个低处的,哥哥便屏住呼吸,蹑手蹑脚地向其靠拢。粘知了最重要的一步是洗面筋,这是我擅长的。我会学着母亲的样子和一块面团,然后在水里一点点将面筋揉好,泡在小碗里备用。发现知了的时候,哥哥便迅速将面筋从水中捞出,裹在细竹竿梢上,然后将竹竿一点一点伸向知了的翅膀。知了会在一声惨叫中被掳获,然后狠命蹬着爪子,扇着翅膀,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声,然而却终难逃脱厄运。
“风蝉旦夕鸣,伴夜送秋声。”一天又一天,一年又一年,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,季节也在它的嘶鸣中交替更迭。如今,几十年过去,再回故乡,摸知了龟的孩子已极少见,粘知了的孩子也不见了踪影。然而,蝉鸣却永远响彻在我童年的记忆里。
(作者作品散见《中国青年报》等报刊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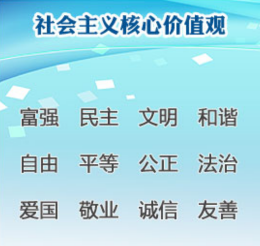
 渝公网安备50011202500163号
渝公网安备50011202500163号 