◎ 谢光明
牛体格壮,力气大,降服它的,不是刀枪棍棒,是人的智慧。古人四两拨千斤,一根软绳拴住软肋,犟牛从此对人类服服帖帖,将牛的力气化作生产力,使牛成为人类创造农耕文明的重要参与者。
《诗经·小雅》:“我任我辇,我车我牛”。古代,牛不仅是生产力,还是一种重要的交通工具。普通老百姓出行喜欢骑牛,圣人出行也喜欢骑。李耳年逾七旬,手捧《道德经》,骑青牛出函谷关。明代画家张路将这一故事画了下来,《老子骑牛图》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。老百姓骑牛,圣人骑牛,腾云驾雾的神仙也喜欢骑牛。太上老君的坐骑就是一头青牛,它趁牛童打瞌睡,忘记拴绳,偷跑到人间,当了一回独角兕大王。
牧童与黄牛,是中国诗人眼中的标配,是理想国世外桃源的标志,是历史深处的烟火味。牛是土气的,牛背是风雅的。“牧童归去横牛背,短笛无腔信口吹”“舟子斜荡浆、牧童倒骑牛”“落日断霞连岳顶,牧童归去倒骑牛”。“倒骑”是一种技能,更是一种境界,与张果老骑毛驴异曲同工,皆带有灵逸的仙气与超越生活的洒透诗意。
牛背上的乘客远不止人类和神仙。牛背鹭骑牛最为显眼,洁白轻盈的身体,曲线优美的脖颈,任凭水牛走动,它在牛背上巍然不动,始终保持平衡的绝佳状态。牛背鹭多三五成群,众星捧月般围着牛,若蝴蝶骚扰周庄。牛背嶙峋的骨骼,是连绵纵横的山脉,突然垂下的牛尾巴,是一溪跌落的瀑布。牛背鹭,牛背上的悠悠白云,飘忽着的是美好人间。还有一些不知名的乘客,比牛背鹭体型小得多的小鸟,甘愿做牛身上的一枚装饰品,贴在牛头,帮牛清理寄生虫。硕大的牛眼之于小鸟,似一泓清池,映照无边无际的天空。
农村孩子放学放假后,是要帮家里干农活的,放牛是其一,也是孩子们最喜欢做的事。说是放牛娃放牛,不如说是牛放放牛娃,哪里的草鲜美,牛比孩子清楚。孩子们只需趴在牛背上,任它走,走哪是哪,不会错。没有牛背鹭和小鸟的时候,孩子要提防牛虻叮咬水牛。牛虻吸牛血,贪婪的肚子胀得像个小灯笼,看得人咬牙切齿。钻进牛肚子抓牛虻,是许多农村孩子共同的记忆。更有那些女孩,把五彩缤纷的山花绑在牛尾巴上,或挂在牛角上,将忠厚老实的老牛打扮得花枝招展。
我曾长时间目睹一头暴风雨中的水牛。密集的雨点炒豆似的洒下来,打得树叶翻飞,水面起泡,树木在风雨中大幅度左右倾斜摇晃。树下一头水牛,在风雨中纹丝不动,安静地闭目养神,细细回味青草的芳香,丝毫不在乎风雨的侵袭。雨点落在牛脊上,升起一股淡淡的水汽,有雨水溅起的氤氲,也有牛身上散发的热气。那一刻,我对水牛肃然起敬。生命的形式不同,灵性相通,不惧风雨是所有生命共同拥有的一种精神。
牛是最温顺的童年伙伴。我也曾是牛背上的乘客,只记得牛背上的时光很慢,慢得永远看不见长大的那一天。可是谁曾想,时光如此荏苒,牛背上的伙伴早已各奔东西,转眼之间,牛背上的故事变成一个遥远的传说。
(作者作品散见《资阳日报》等报刊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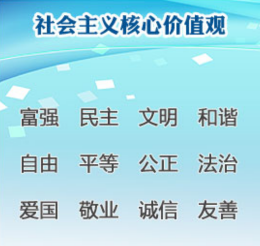
 渝公网安备50011202500163号
渝公网安备50011202500163号 