◎ 王应兰
父亲执意要回老家,这一次,谁也无法阻止。
天蒙蒙亮,父亲慢慢地走进风里。村公路、河边的土路、田埂……春天有着温柔的绿色,远远近近似波浪起伏。
自母亲走后,父亲便没有了春天。此刻即是永恒,父亲清晰地看到了,并伸出手去,想要抓住它们。
每走一步,天就亮一寸,直到天亮得通透。父亲不说话,就像雨一直没有下,悬在每个清晨,沉默着。他的脚印在每一处经过的地方留言。
家门前的小河,前几年我才知道它是有名字的,叫小安溪。曾经,父亲从河里挑水浇菜;在河里一边饮牛,一边给自己洗澡;农闲时,坐在河岸边钓鱼……他做这些的时候,总有母亲在远远地凝望。河水涨落,应和着村庄的白天和夜晚,也应和着父亲母亲平淡的生活。
有时,父亲一个人在泥土里侍弄,天空是明朗的。父亲耳朵有些背,但是他能听到泥土深处的声音,每一寸土里都有锄头的声音、镰刀的声音、犁铧的声音、牛的声音……还有庄稼在农时里抽穗、灌浆的声音,以及成熟时无比饱满的欢呼。
有时,父亲挑担,母亲背筐;父亲打窝,母亲点种;父亲在前面不紧不慢地走,母亲在后面一边唠叨一边跟随。
泥土躺在蓝天下,默默无语。他们的脚印在那里,日复一日,重重叠叠;他们的气息留在那里,彼此交融、蒸腾,飘散在风里;他们说过的话,像珠子似地一颗一颗坠落,藏匿在泥土鲜活的呼吸里。
母亲嗓门大,遇事咋咋呼呼的,父亲习惯于她的喋喋不休,憨憨地笑。偶尔被惹急了,也会吹胡子瞪眼,或厉声呵斥,母亲立刻就不作声了。
母亲走后,世界似乎都安静下来,父亲愈发沉默。他牵着小黑狗,在小区里独自走着的时候,没有虫子的私语,没有小鸟的鸣叫,无限的黑暗便开始蔓延,直到把他们深深地淹没。
他的身边,应该永远有母亲的。
母亲突然离去,我也一点儿心理准备都没有。
家里,到处都是母亲的身影,到处都能听到她在说话。我总是四下张望,想寻她出来。这样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,我终于清醒,母亲是真正地离开我了,再也不会回来。从此,我就是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了。我想父亲也是这样的。他那段时间常常做梦,看到母亲还在他身边,醒来,枕边人却不见,眼角挂着泪滴,悲伤得不能自已。
少年夫妻老来伴,父亲永远地失去他的伴了,他的世界自此孤寂。
但父亲终是不甘心的,他执拗地回到老家,那里有他和母亲的大半生。他在这个唯一熟悉的地方寻找母亲,一直都在寻找。他的脑子经常迷糊,他总相信有一天能找到母亲,日子能回到从前。
父亲躺在那张已沾满灰尘的旧木床上。他说:你们两姐妹都是在这张床上出生的。我相信,母亲一定听得见。是的,这是我们生命的伊始。几十年过去了,时间飘散在各处,或许,它们从未离去,一直停留在这里,只是躲在了某个角落,只等记忆来唤醒。
门前的那丛竹林,那几株桃树、李树上,仍停留着母亲的呼唤,悠远又陌生。绿叶在风中摇晃,仿佛母亲的手的温度还在。
没有了母亲,父亲老得很快。他再也不能种庄稼,眼巴巴地看着土地荒着,长满杂草和树,成了另一个郁郁葱葱的世界。
父亲在院子边上种上一些蔬菜,殷勤伺候,以种庄稼的心情、使命和责任。南瓜开了花,丝瓜爬上架,泥土又活了过来,父亲逝去的光阴,都一寸一寸回来了。清晨或黄昏,父亲长久地凝视着,他的目光慈爱地抚过,浑浊的眼眸也明亮起来。他心里想的,都在默默地说给泥土,似乎在等待着泥土的回答,这些生命的语言,只有泥土懂得。
(作者系重庆市铜梁区作家协会主席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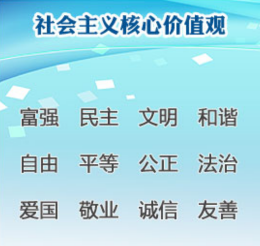
 渝公网安备50011202500163号
渝公网安备50011202500163号 