◎ 尚庆海
父亲是个慢性子,做什么都是慢腾腾的。父亲干活慢,母亲割麦,一天能割差不多一亩地,父亲却只能割三分地;父亲吃饭也慢,每次都是母亲在等着洗碗,催促着父亲吃快点。父亲极爱抽旱烟,但他还在用大拇指往烟斗里摁烟丝的时候,别人已经把烟灰磕在鞋底下碾灭了……
也许是父亲的缘故,我们家的光景过得非常艰难。仅凭几亩薄地要把我们兄妹几个养大成人,慢性子的父亲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。农忙一结束,不用母亲催促,父亲就会到县城的工地打小工,干一天日工两块五角钱,父亲从来不舍得乱花一毛钱,哪怕是几分钱一盒的卷烟,也是舍不得买的。
父亲辛辛苦苦打小工挣的钱,永远也不够我们兄妹几个的学费,一家子一年四季穿母亲粗布缝的衣服,每顿饭都少不了从田间沟边挖来的野菜,一篮子一篮子被母亲洗干净摁进锅里。
那年,二哥得了阑尾炎,肚子疼得厉害,去乡卫生院买药,家里没有钱,父亲就出去借,母亲见父亲还是那副不紧不慢的样子,忍不住埋怨,你一辈子都这样磨磨蹭蹭,就不会跑两步?又笨又慢……这啥时候是个头啊?母亲说着抹起了眼泪。
母亲埋怨父亲慢得像只蜗牛,我也学母亲的样子说父亲像只笨蜗牛,父亲听了,只是对我和蔼地笑笑。后来,父亲患了腿疾,走路一跛一跛的,本来就慢腾腾的父亲就更显得笨拙了。没有工地愿意要父亲,父亲只好跟着母亲到处开荒,沟边房后,什么都种。
邻乡开了一个煤矿,一车一车的煤矸石运到矿外面,堆成了一座小山,村里的人都到煤矸山上捡煤炭,每次都能捡上半蛇皮袋子。父亲见了,也在腋下夹了一只蛇皮袋子跟着村人去捡煤炭。煤矸石里哪有那么多的煤炭可捡,原来都是趁煤矿里的保安打盹的时候,跑到矿里偷煤炭,父亲不去偷,回来的时候,人家都背着半蛇皮袋子煤炭,父亲的袋子里只有牛蛋大那么一点。
母亲看着老实巴交的父亲叹气,父亲笑着一字一顿地说:“没事,大不了我到煤矸山上跑起来,一直跑在他们的前头,还怕捡不来!”第二天,父亲天不亮就出发了,我刚好起来上茅房,在明晃晃的月亮下面,我真的看见父亲是跑着到院子门口的,不过父亲的身子左右颠得非常厉害,模样很滑稽,速度却和他平常走路没啥两样。
那天父亲带了两个榆钱窝头做干粮,中午没有回家吃饭,晚上回来的时候,蛇皮袋子却空空如也!看着满身满脸沾满煤屑的父亲,母亲的脸上写满了疑问,父亲不紧不慢地说,邻村跟着后娘过的小孬你知道吧?才十一二岁,他也去捡煤炭,回来的时候把煤炭放在路边去沟里拉屎,他的煤炭不知道被哪个缺德的孬种偷走了,只给他留下了一只空袋子,小孬好生地哭,他不敢回家,怕他后娘打他说他在外面跑耍了,我看着可怜,就把捡来的煤炭都给他了……
母亲听了,这次没有叹息,把一碗榆钱糊涂递给父亲。
有天半晌午的时候,村子里捡煤炭的人三三两两回来了,有的满脸丧气,有的惊魂未定,嘴里还骂骂咧咧的,原来是矿里对偷煤者采取了行动,很多人都被煤矿的保安逮住了。
母亲心想父亲不偷,没事。可下午的时候,村长来说父亲被煤矿的保安逮着了,要父亲把之前偷来的煤炭都交出来,不然就罚钱。交什么煤炭?家里根本就没有煤炭可交,于是父亲被迫在煤矿义务采了一星期的煤。后来我们才知道,那天保安截堵,偷煤者都往煤矸山上跑,想浑水摸鱼,逃脱惩罚,保安不管那么多,只要逮着一个就算一个,慢腾腾的父亲是第一个被逮着带到煤矿的。经历了这件事后,父亲再也不去捡煤炭了。
父亲满怀内疚地宽慰母亲,没事,我慢不要紧,以后,我跑起来,别人走,我跑,我跑起来咱就慢慢不落后了。
从此以后,父亲真的开始奔跑起来了,不管是跟着母亲去开荒,还是偶尔去做一点小买卖,甚至上茅厕,父亲都是把双臂弯曲,做出了奔跑的姿势。
那年夏天,水库放水,村人都去北大河里捞鱼,父亲也想给我们捞鱼吃,就用一根长长的竹竿做好了捞鱼的工具,奔跑着往北大河赶,赶到北大河的时候发现,河两边黑黑压压都是捞鱼的村人,父亲就往前面挤,当终于挤到前面的时候,却被村人不小心碰了一下,一个趔趄,掉进了暴涨的河水里,好在河两边都是手握长杆的人们,父亲才逃过一劫。
当父亲被村人搀着进院子的时候,看着脸色苍白,浑身湿漉漉的父亲,我被吓坏了,忍不住朝他奔去……
(作者作品散见《人民日报·海外版》等报刊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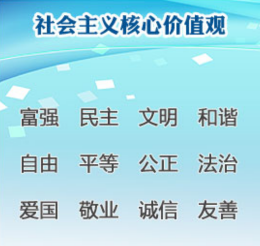
 渝公网安备50011202500163号
渝公网安备50011202500163号 