◎ 李万碧
常常想起家乡老房子拆迁以前,不远处的那座山丘。那山丘上,驻足着我一段时光。
那时,我和我的小伙伴,放学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割猪草。不远处的山丘,是我们割猪草必去的地方。我们常常坐在被割空了的猪草地上,仰望深蓝的天空,朦胧的意识里,这可以解除我们的烦恼。有时候,我们躺在草地上,有伙伴会发出感慨:“天空其实没啥看头,蓝得一丝云彩也没有。”说完,晃了晃脑袋望向我们,看看我们是不是有同样的想法。
每次割完猪草后,我们总会到山丘下的溪水中洗手。那青草的翠绿汁液早已浸染在手指和掌心,任我们反复搓洗,难以将其彻底清除干净。我们停止打闹时,回望那座山丘,它静静地矗立于眼前,骄傲而又自在。
更多的时候,我们会站在山丘顶,极目远眺。山下的田野被参差不齐的地块所形成的波浪切割开来,乡村的房屋就坐落在这波浪起伏里,那些泥巴筑起来的土房,宛如一朵朵蘑菇。俯瞰与近看的感觉截然不同。
毕竟是贪玩的孩子,阳光还剩半个山丘时,我们就会进行一场特别的“游戏”——寻找妈妈。这是我们最开心的游戏,乐此不疲。游戏开始前,大家兴致勃勃地商量好规则,谁要是找错了自己的父母,就得接受处罚。而我们的处罚方式也简单有趣——让找错的人去割一背篼猪草,然后平均分给大家。
放眼望去,原野上绿色、蓝色、青黄色的植物交错起伏。妈妈们在这起伏的庄稼地俯身拔草,身影时隐时现。阳光洒在她们身上,即便相隔甚远,我们也能从他们劳作的姿势辨认出各自的妈妈。她们不时侧头与身旁的人交流,虽然我们不知道她们在谈论什么事情,但从姿态可以看出,她们笑得很开心。她们将拔下的部分野草抛向路边,这些野草可是宝贝,带回家作为喂牛的饲料。
唯有我的母亲,与其他人稍有不同。她自始至终都没有直起过腰,只是不紧不慢地向前拔草。虽然她们开始劳作时在同一起点,然而随着进度的推移,小伙伴们的妈妈总是远远地落在我的妈妈后面。
如若遇到一阵清风吹过,带起庄稼的叶子集体起舞,将妈妈的身影恍惚起来,仿佛离我们很远很远。山丘的天空,又常常有鹞鹰、喜鹊、大雁飞过,还有那些在这里安家,生娃,繁衍着一代又一代……这掠过地面的风,那些在天空飞翔的精灵,时常会凌乱我们寻找妈妈的眼睛。于是,在起哄的催促里,小伙伴们就常常认错远处的妈妈。哈哈,那就只能接受惩罚了。
故乡的山丘啊,当时光远去,我再次回到已经变了模样的老家,要不是那些留守的乡亲,还保留着岁月沉淀给他们各自的个性,以及他们用自己个性装点的钢筋混凝土房屋,我还真不好寻找故乡记忆。我想起不远处那个山丘,好在山丘的外貌依旧。
我以一种仰望的姿态,沿着山脚缓缓前行。上至山丘顶的小径上,一朵朵野花在努力盛开,它们仿佛是每个日子里的山丘,那么圆润,又那么风光无限。但愿我的山丘,一年如此,十年如此,年年如此。
我缓缓行走在山脚,山腰上懒散的山羊悠然自得,像山丘顶上悠闲的云。这一刻,我的眼眶湿润了。我想起一起割猪草的小伙伴,想起那句:“天空其实没啥看头,蓝得一丝云彩也没有。”
(作者系重庆作家协会会员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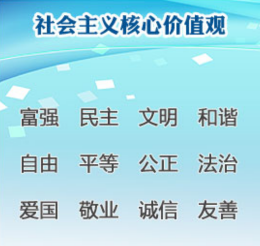
 渝公网安备50011202500163号
渝公网安备50011202500163号 