◎ 王志荣
“我和你妈妈必须立马去北京。”父亲头也不抬,只顾匆忙收拾行李。我看到他把身份证、退伍军人证和几张面额不同的存折塞进背包最里层的拉链袋。
我知道是何事,只是害怕问明白。
“你妈妈病情严重,耽误不得。”父亲继续埋头把衣物等必备的东西码进行李箱。
临别时,父亲表情有些焦灼。母亲不知自己身患乳腺癌晚期的实情,稍显平静,她反复叮嘱我哥俩的吃穿安全等日常琐事。我隐隐担忧这是母亲最后的唠叨,判若两人地顺气地倾听着。
我清楚,年得靠自己熬过去。
“大年三十晚上……我会打电话回来的……”母亲哽咽着说完话,转身上船,留下头戴雷锋帽的孱弱的背影和那句话在浮桥上逐波摇晃。那句话仿佛成了我们母子之间的生死约定,沉重又充满希望。我攥紧拳头,心里默默祈祷:妈妈,除夕,您一定要平安如约。
到北京五棵松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后,父亲只给我们来过一次电话,说入院、检查都顺利,稍微调理好母亲的身体,年前就要做手术,此后再无音讯。离除夕近一天,我心中的忧虑就增加一分。
除夕,家里异常冷清,哥哥从不碰家务事,我做了二三样简单的菜,哥俩就着米饭吃。回想起以前家人围坐一桌热热闹闹吃团年饭、看春晚的情景,我顿时悲从心起,胃口全无,草草吃完了事。
那时,我家还没安装电话,只能依靠父亲单位传达室的聂爷爷转唤。腊月的深夜,室外寒气袭人。办公楼到宿舍楼来回得走十分钟左右,不愿麻烦聂爷爷来楼下喊,或许是太迫切,我索性到传达室去等。
传达室仅有聂爷爷一个人,陈设简陋。在一张桐油色的办公桌上,左边立着一台14英寸黑白电视机,右边搁着一台米灰色电话。互相寒暄几句后,我在距离电话稍近的一边坐下,他继续煞有兴致地看春晚,身前一膛通红的炉火抵御着寒冷的侵凌。
一会儿,铃声响起,我兴冲冲地去接,听筒里传来陌生的声音,我只得失望地把接听器递给聂爷爷。后来几次响铃,我都没敢再接。我无心观赏电视里优雅的歌舞曲艺、搞笑的相声小品,时不时瞄一眼电话。可它像一只冬眠的青蛙,毫无动静。我等待它苏醒,如坐针毡。
直到凌晨零点,电话再没吭声。电视里敲响了新年钟声。窗外鞭炮、烟花骤然齐鸣,寂静的小城瞬间沸腾起来,黑黢黢的夜色被炫彩的焰火点亮。可这一切与我有关吗?不过是别人家的狂欢。
十几分钟后,那些喧嚣声和炫彩焰火消失,炉火渐熄。聂爷爷耷拉着脑袋似睡非睡,模样困倦。我主动关了电视,夜沉寂下来,静得寒凉沁骨。唯有墙上挂钟一秒一秒的脚步声在我的心上爬行。我比兔子还要警惕,竖起耳朵监听随时可能响起的铃声。挂钟啊,你爬慢些!不,你爬快些!
难道忘了?或许手术不成功?我暗自揣测各种可能,越想越失落,越想越惶恐。我感到身体已冻成了一根冰凌。
近零点三十分,我已完全不抱任何希望,正准备离开时,铃声蓦然响起,那铃响声振屋瓦,像电流刺激着我的神经。我猛地回身跨过去,一把抓起手柄,听筒里传来母亲极其细微而颤抖的声音:“你们一定要学会照顾自己……你要走正道,远离混混,否则就会像生了蚜虫的庄稼一样夭折……”我听出她已知晓自己的病情,对我最放心不下。我极力控制情绪,但眼眶像裂了口的热水袋,泪涌不止。我顾不得羞涩,泣不成声地对着话筒呼喊:“妈……我改!”
太多预想的话在那一刻竟无语凝噎。
母亲曾给我讲过熬年的故事,说熬年也叫守岁,传说可以祛除邪魅病疫。为了熬走纠缠母亲的病魔,我宁可信其真。那夜,我终究没合眼,屋里灯火通明,脑子里浮现的全是母亲的影像。
磨砺是最好的催熟剂。那年那个除夕,熬年的我,“熟”了。
(作者单位:重庆市云阳县青龙街道复兴小学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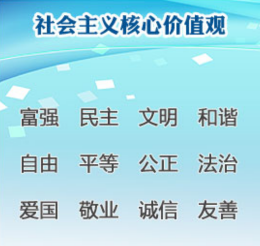
 渝公网安备50011202500163号
渝公网安备50011202500163号 