◎ 翟智慧
那年的腊月二十八,天出奇地冷,母亲忙着蒸馒头,便让我领两个弟弟玩。
那年,我八岁,大弟六岁,小弟三岁。
我领着两个弟弟来到窗前,刮开窗户上厚厚的窗花,但见瘦削的父亲正在劈柴。冰天雪地里,父亲头发上的汗水凝成霜花,在凛冽的寒风中倔强地竖立着。
这时,姥爷来了。他在屋里转了一圈,问母亲:“过年啥也没买呢?”母亲嗫嚅地“嗯”了一声。姥爷叹了口气,从兜里掏出十元钱塞到母亲手里,转身回家了。
过了一会,姥爷又折回来。从怀里掏出个纸包,一层层打开来,是一小条猪肉。母亲面露喜色,那年月,一般人家过年也就买两三斤肉,那一小条肉很珍贵了。
太阳偏西,家里添客人啦,母亲便把肉煮上,又拿出冻得硬邦邦的鸡杂,用菜刀砍下一大半,加了土豆炖上。腊月杀了几只鸡,母亲全都卖掉了,只留下一些鸡杂准备过年吃。
我们仨都在厨房站着。母亲喊了几遍,让我领着他们出去玩,我也没动。肉味太香,实在挪不动脚啊。
肉熟了,在案板上白亮亮、颤悠悠的,简直馋死个人。母亲把肉片切得极薄,一片挨一片摆在盘子里,勉强摆了两层。母亲留下几片肉放在小碗里,盯着小碗瞅了一会,轻轻叹了一声,又把肉捡出来,放进盘子。
她勉强凑了四个菜端上桌,那时家里来客人,女人和小孩不能上桌。但母亲不忍看大弟的馋样,说:“大小也是个男人,你上桌陪客吧。”说完又附在他耳边小声地说:“记住了,只能吃三块肉,不准多吃啊。”
大弟夹了三片肉后,就不再往猪肉盘子里伸筷子,转而去夹鸡心。鸡心没有切开,圆圆的,在筷子间不住打滑。大弟咬着嘴唇,小手费了半天劲,才夹起鸡心,没等送进嘴里,鸡心就从筷子上滑落,骨碌碌翻滚到客人碗边。母亲咳嗽一声,他赶紧把伸出去的小手缩回去,偷偷看了客人一眼,没敢去捡鸡心,也没敢再去盘子里夹菜。
好不容易等客人走了,小弟欢天喜地爬上桌子,却哇地一声哭了,嘴里叫着:“啥都没了,全都吃光了。”我不知怎么哄他,因为我和他一样难过。大弟站起身,用手捡起那颗已经凉透的掉落的鸡心送到小弟嘴边说:“这还有一个,你吃吧。”小弟咀嚼着鸡心,终于止住哭声。
母亲盛了一碗米饭倒进鸡杂盘子,浓稠的汤汁瞬间被米饭吸收。我们姐弟四个每人一份,小弟大口嚼着饭,含混不清地说:“真香,是肉味儿。”母亲又用煮肉的汤炖了两大碗白萝卜片,小弟也不住地说:“有肉味儿。”
腊月二十九,父亲发工资啦,他去集上买了一大块肉和两条冻鱼。氤氲的雾气里,屋里又飘出了煮肉味儿。母亲切了一盘子肉说:“这回吃吧,管够!”小弟终于吃到猪肉,眼睛笑成了弯弯的月牙儿。
我们吃得满嘴流油,无暇他顾。直到姐姐夹起两块肉放进母亲碗里,我才发现,母亲一直在吃炖萝卜。我也赶紧给母亲夹了两块肉,俩弟弟有样学样,都夹了肉往母亲碗里放。母亲用手捂住碗,连说:“够了够了,妈吃不了,你们吃吧。”
又到新年,满桌山珍海味,为我们操劳一生的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,看着一群孙男娣女,觉得哪个都好看,哪个都喜欢。她破天荒地拿出姥爷留下的小酒盅,非要跟大伙对饮几杯。
席间,孩子们的手机叮叮咚咚地响着,贺岁红包、祝福短信发个不停。嘴里不时蹦出时下的流行词语,母亲听不懂,也插不上话,便不停地给孩子们夹菜。
她给每人夹了两片五花肉。外甥勉强吃了一片,女儿略带为难地把肉夹出来,说:“姥姥,肥肉对身体不好,你也得少吃点呀,现在都提倡健康饮食呢。”女儿关切地说。
“姥姥这身体好着呢,没事。”母亲说完,又拿起酒瓶,给自己倒了满满一盅酒。抿了一口后,夹起一片肉,蘸了蒜泥放进嘴里慢慢咀嚼着,说:“现在的孩子都不爱吃肉了。你妈她们小时候啊,一顿都能吃一小碗肉。”
顿了一顿,母亲又悠悠地说道:“现在的猪肉,再也吃不出当年的味了!”
母亲难忘的只是那年的肉味吗?物质匮乏年代,口腹之欲的满足让人难忘,亲人间深切的理解和浓浓的牵挂更让人挂怀呀。
年,对我们来说是一份对家的牵挂和美好生活的期盼,不管以前如何,现在怎样,年味在变,人情味却始终未变,和家人团圆便是最好的年。
(作者单位:河南省洛阳市汝阳县人民检察院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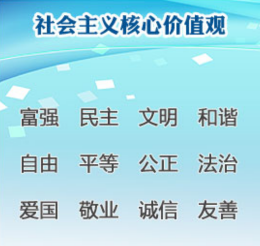
 渝公网安备50011202500163号
渝公网安备50011202500163号 