◎ 孙秀斌
1953年的深秋,大伯和一位朴实的农家姑娘坐火车,乘轮船,舟车劳顿地来到了嵊泗马关父亲的营房。曾经介绍父亲入党的大伯,又当起了红娘,为弟弟的终身大事操心。那时的父亲是一名年轻的军官,英俊潇洒,威武倜傥,腼腆的母亲只看了一眼,就已是脸色绯红,心中如小鹿乱撞了。而母亲农家姑娘的淳朴贤惠,心地善良,也博得了父亲的欢喜,大伯介绍的人肯定不会差。就这样,父亲和母亲一见倾心,定下终身。一间简陋的营房,两个柳条箱子,是全部家当,几位战友在一起吃了顿饭,就算婚礼了。婚后,相濡以沫的父母共同生活了24年。
婚后10年里,母亲生下我们兄妹四个,我是老大。那时候父亲军务在身,无暇顾及家中事务,全都是母亲一个人承担,一家六口的一日三餐,柴米油盐,浆洗缝补,可以说相当辛苦,但母亲从未抱怨过,因为她知道嫁给军人就意味着要付出,擅长女红的母亲,把一个家料理得井井有条,小日子过得是红红火火,有声有色。
然而天有不测风云。1964年初,一天,父亲腹痛难忍,煎熬一夜后去部队诊所就医,不见好转,后转院经专家会诊怀疑是急性胆囊炎,需要立即手术。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和技术,父亲手术后又发生了肠粘连,不得不动了二次手术。短期内的两次手术使父亲大伤元气,身体十分虚弱。本来是要在部队疗养院住上两个月的,可是父亲拆了线不久就要求出院,因为那时母亲快要分娩了,父亲心中牵挂,哪里还有心思疗养。那年的春天,我的最小的弟弟出生了,那时候母亲心里是喜忧参半,喜的是又添了一个儿子,忧的是父亲这虚弱的身体,自己身上的担子更重了。
次年,因为身体的原因,父亲转业了,我们全家来到了地方。在地方父亲担任了一家单位的书记,可那时父亲又罹患高血压,常常飙升到高压200多,由于血压控制得不好,几年后父亲得上了脑血栓,半身不遂。瘦弱的母亲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,那时候父亲血压高休息不好,常向爱争吵的我们兄妹几个发火,我们都十分怕他。可是无论如何,父亲都不曾向母亲抱怨过,因为母亲对父亲太体贴了,可谓是举案齐眉,相敬如宾。在我的记忆中,父母不仅没吵过架,脸也未曾红过。在那物资匮乏,生活拮据的年代,母亲总是想方设法每天炒两个鸡蛋给父亲滋补身体,因为常常买不到鸡蛋,后来家中养了几只母鸡下蛋,用来救急。因为母亲知道,父亲是这个家的顶梁柱,他一旦倒下了,那可就难了呀。
父亲是个不会浪漫,嘴巴极拙的人,在我的记忆中,他从未称呼母亲什么。据母亲说,在第一次见我的姥姥时,母亲曾嘱咐他到时要喊“妈”,可到见了面,父亲脸憋得通红,愣是没叫出那个“妈”字。不过母亲并不为此生气,她知道嘴巴拙的人,内心的守望会坚如磐石。果不其然,“此处无声胜有声”,在长达24年的婚姻里,父亲从未说过母亲一个“不”字,家中财政大权全由母亲来掌握,尽管母亲只有一年私塾的文化水平。
母亲人缘极好,家中的人情来往全由母亲张罗。父亲的同事和战友来家中做客时,全是母亲操持,因为倔强耿直的父亲常常会得罪一些人,有时需要母亲来圆场。因此认识我父亲的人都会说,你真有福气,找了一个贤惠善良,能言善语的媳妇,为家撑着门面。
或许是天妒良缘,母亲1977年突发重病,医治无效,才46岁就离我们而去。正当我们兄妹悲痛欲绝,哭得稀里哗啦的时候,父亲却异常地镇静,并未嚎啕大哭。难道他会像庄子一样“击鼓而歌”吗?非也!他哪有庄子那样的境界,命运多舛,半身不遂的父亲已没有力气哭了,他不想让中年丧妻的悲痛再击垮自己,他需要坚强,因为还有四个孩子正在成长。大伯来了,他把母亲的骨灰带回了老家,让她魂归故里!
如今,我的父母都早已去了遥远的天国,但我时常会在梦中想起他们。在天国里安睡,不知父母听说过七夕的故事没有?但愿这一天他们能相见,像当年在嵊泗马关营房初相见时,心如鹿撞,爱如潮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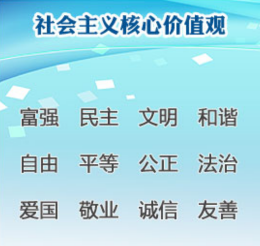
 渝公网安备50011202500163号
渝公网安备50011202500163号 