◎ 刘开伦
早上一刷朋友圈,老家已铺上了厚厚的积雪。我的故乡在重庆市石柱县海拔1500米的高山上,二十多年前我上小学的时候也是这样,总要冰天雪地一段时间。
一觉醒来,屋外的树林披上了银装。推门之间,雪光照的人睁不开眼。但再大的雪,都阻止不了乡村小学朗朗的早读声。
“呼呼呼,哐当哐当”母亲总是第一个起床,用钢管制作的吹火筒生火,砸烂水缸里的冰块烧水,给我准备早饭和装好带到学校吃的午饭。一切都完成后,就开始一遍一遍地催促我起床。
蜷缩在被窝的我,感觉在耳朵开始起茧子的时候,爬起来缩着脖子迅速洗脸吃饭后,挎起青布书包,拎起小火炉上学了。
屋外,雪白的雪从脚尖延伸到远山,几只麻雀从矮树中掠过,路中间,狗的梅花脚印如交响乐般跳跃向前。
和邻居小孩深一脚浅一脚“咔嚓咔嚓”踩在松软积雪,一路上竟有着莫名的兴奋,走着走着直立倒下,在雪地上印上一个个人形,脖子钻进一撮撮雪花,透心凉。
这时候,提着的小火炉就派上用场——暖手。我的小火炉是用一个废弃的油漆罐子做的,在罐子底部打上几个小洞透风,罐体上沿打两个洞穿上铁丝作为把手,出门的时候底部放上木炭,母亲再把火塘里红彤彤的烧着的木炭夹几个放里面,最上面盖上一层热的草木灰。这样既可以路上暖手,里面的木炭还不至于燃烧太快。
到学校后,我们先用上十来分钟把小火炉的火倒进大火盆里,大火盆里放着大木炭,也有的孩子因为家里没有大木炭,脚底下就只有个小火炉。大木炭的烧制对木材品种以及温度控制要求都很高,我的父亲每年下雪天都跑“山那边”烧炭,一部分卖钱,余下的就供家里和我上学生火。
火生好后,同学们一个个脸上、手上沾着碳灰,瞪着清澈的双眼,开始听老师上课。老师只是山村里临时指派的,但我始终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厉害的老师,一个老师教两个不同年级的班,这个班讲完布置完作业就到下个班讲课,课程进展很顺畅,每周还会给大家教上一首歌。每当这时,火盆里的木炭燃烧发出噼啪的炸响,偶尔还弹起几颗火星,整齐划一的童声穿透糊着报纸的窗户,飞向白雪皑皑的山村……
中午,我们各自把饭盒放在火盘上,不一会儿,夹着饭和菜的盒子咕嘟咕嘟起来,要是杀了年猪,就有着被同学艳羡的肉片、猪肝。那时候,还是有个别同学家里特别贫困,甚至中午就只带了点炒得半生不熟的包谷籽,外面抓一把雪就吃下的。
当然,物质的匮乏影响不了孩童的我们在课间冲出教室,堆雪人、打雪仗、拉雪橇……肆意的欢乐中,把童年的记忆挥洒在冰雪的怀抱中。
傍晚,一天的课意犹未尽,踏雪而归,母亲早已把屋子的火生得暖烘烘的,像接待英雄般一边给我烤湿裤子湿鞋,一边埋怨我肯定回家的路上去“划船”了。
暴雪天的晚上,电肯定是没有的。靠着燃烧的火炉,就着一盏昏暗的油灯,我开始阅读白天在学校想方设法从其他孩子那里得到的《萍踪侠影》《雪山飞狐》等武侠小说。每当这时,听觉总是特别灵敏,屋外“咔嚓”踏雪而过的声音,总让我感到有“剑客”在雪夜行,我会马上跑出门去一探究竟,希望能雪夜拜得名师,学成一身顶尖武艺,仗剑走天下。
可惜,小学毕业后,我便一直在外求学、工作,冬天的故乡也开始不轻易下大雪了。偶尔回乡,儿时的玩伴已不知所踪、熟悉的老人已经故去、学校也早已破败挪作他用,每回一次,便心疼一次、思念一次。等到爸妈移居城里后,冬天的故乡,便再也没有了我的身影。
但我知道,总有一天我会荣归故里,成为故乡冬天雪地里的一抔黄土。
(作者单位: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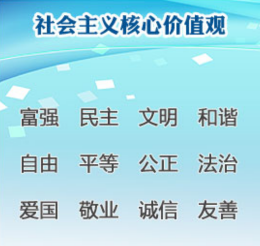
 渝公网安备50011202500163号
渝公网安备50011202500163号 