◎ 徐光惠
在我十岁那年冬天,下了一场多年不遇的大雪。鹅毛片似的飞雪从天而降,无声地飘了整整一夜。
清晨,雪小了些,但仍没停的意思。推开门,天地白茫茫一片,房顶上、树枝上、院子里都积了厚厚的一层雪。母亲老早就起床生火,熬了一大锅热乎乎的红薯粥,年迈的奶奶提着刚生起炭火的烘笼,倚在堂屋门口,咧着掉光了牙的嘴直乐,孩子们兴奋地在雪地里疯跑、打雪仗,清脆的欢叫声震落了树枝上的雪。
喝了一碗热乎乎的红薯粥,全身顿时暖和了许多。母亲拿着笤帚来到院子里扫雪,突然脚下一滑,重重摔倒在地,结果把腰给扭伤了,痛得很厉害,只能躺在床上,翻身都困难。傍晚时,母亲又发起烧来,瘦削的脸庞烧得滚烫。奶奶急得不行,赶紧找电话告诉了父亲。
父亲在离家十三公里外的小镇当养路工人,因交通不便,一天仅有一班车,父亲一星期或半个月才回家一次。每天扛着铁铲、锄头修补公路上的坑坑凼凼,铲泥沙、通水沟,又脏又累,但父亲工作一贯兢兢业业,回到家还挑水、劈柴,从没喊过累。
父亲听了非常担心,他恨不能马上飞到母亲身边,但此时班车已经没有了,父亲决定步行回家。天色已晚,不能再耽搁,父亲随即戴上帽子,穿上翻毛鞋,裹紧身上的棉大衣,揣上半瓶二锅头上了路。
夹壁墙屋子里,昏暗的灯火摇曳。听说父亲要回来,母亲就靠在床头等,不时听着门外的动静。她的烧一直没退,迷迷糊糊的,半眯着眼不肯睡。
刺骨的寒风一阵紧似一阵,直往衣领里钻,雪花在寒风中恣意飘舞。远山近树一片苍茫,除了雪,见不到一丝杂色。路上看不到一个人影,只有脚踩在雪地上发出的“嘎吱”声,风裹着雪花像刀一样割在脸上,生生地痛。天很快被黑色幕布笼罩,天地间漆黑、沉寂。雪地湿滑,路上尽是坑坑洼洼、坡坡坎坎,借着手电筒发出的一点微光,父亲深一脚浅一脚一步一步艰难跋涉。
雪,越下越大,越来越密,湿漉漉、沉甸甸的。父亲的脚步变得愈发沉重,跌倒了爬起来,又跌倒又爬起来。累了,就停下喘口气继续走,冷得实在熬不住了,就喝一口二锅头提提神,他甚至不敢坐下休息片刻,他怕坐下去就再也站不起来。父亲心中只有一个念头,无论风雪再大,无论这路多难走,都不能阻挡他回家。
转过最后一个弯,穿过一片水田,父亲的体力几乎消耗殆尽。远远地,路边人家窗户透出星星点点的灯火,终于快到家了!父亲来了精神,不由加快了脚步连走带跑,朝着家里的灯光奔去。
“咚咚咚、咚咚”,深夜十一点半,父亲的敲门声终于响起。十三公里的路程,父亲在雪地里艰难行走了整整五个半小时,才回到了他深深牵挂的家。
打开门,寒风猛地朝屋子里灌,父亲满身雪花站在门口,一脸疲惫,浓黑的眉毛上也挂着一片晶莹的雪花。
“孩子妈,吃药了吗?好点没有?”父亲来不及抖落身上的雪花,几大步来到母亲床前,拉住母亲的手。
“孩子爸,你回来干啥呀?二十几里地儿,就这样走回来的?一定累坏了吧?”看着父亲脚下湿淋淋的一滩泥水,母亲的脸上,早已是泪雨纷飞。
“路滑不好走,等急了吧?”父亲眼里流露出焦虑和无尽的温柔。
“孩子爸,真是难为你了,快坐下歇歇吧。”母亲说。
夜里,为了让母亲的烧尽快退下来,父亲每隔一段时间,就将毛巾用冷水打湿后放在母亲的额头和手腕,间隔一会儿又换一次,还用白酒擦在母亲的手心和脚心进行降温。
“孩子爸,不用管我,你快去睡吧。”母亲痛得难受睡不着,却又心痛父亲跟着她受罪。
“没事儿,我陪你说说话呵。”父亲说啥也不肯去睡,有一搭无一搭和母亲说着话。不知不觉,天就亮了。那一夜,父亲守在母亲床前寸步不离,整整一夜没有合眼。
窗外,天寒地冻,雪花,依旧纷纷扬扬。屋子里,父亲和母亲执手相望,温润如春。
(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,作品散见《人民日报》等报刊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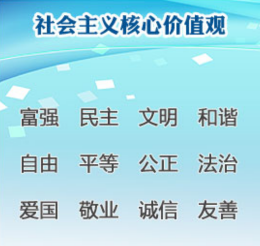
 渝公网安备50011202500163号
渝公网安备50011202500163号 