◎ 史良高
腊月,是一枚风风火火的动词!
吃过了腊八粥,故乡小镇便一天比一天地热闹起来,嘈杂的市声每天就像一锅煮沸的豆浆,从早到晚漫溢得满街满巷。
腊月,学校早早地就放假了,一群从笼中放飞的“鸟”快活得横冲直撞,如一只只振翅高飞的云雀。下街头水府庙边的旧戏台,成了我们极好的练功场。戴上悟空、八戒、关云长的“鬼脸壳”,操根树棍、晾衣杆,就把“西游”“三国”上演得淋漓尽致。找来稻草、高粱秸扎成长长的龙灯,画上威武的龙头,大张的龙嘴,糊上红蓝黄绿的彩纸,沿街也能舞出一道嘻嘻哈哈的风景线。
腊月的茶馆那才叫茶馆,跑堂的小二拎着长嘴大铜壶,一个转身壶就干得见了底。炸油条、麻花、锅巴的水爹、水奶,忙得头上直冒热汗总是供不应求。从外地返乡的包工头、贩鱼花(鱼苗)的老板挑夫和老实巴交的庄稼汉,都喜欢聚在这闹哄哄的茶馆里,相互交流一年来的酸甜苦辣,聊一聊外边的精彩世界,探讨来年的致富信息。爱凑热闹的人们,把猴戏演在茶馆门前的空地上,不时地逗得茶客们一阵阵哄堂大笑。吃饱喝足笑够的人们这才想到快近晌午了,于是担着一担年货,带着一脸微笑,春风满面地踏上回家的路。
商家的腊月是一年中最繁忙的日子,柜台前除了涌动的人头还是人头。一船船年货从湖边码头走上了货架,不几天工夫便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服装、布匹、鞭炮、年画、日用品,没有一样不非常地走俏。入夜,店铺里家家灯火通明,噼里啪啦的算盘声一家比一家打得亢奋爆响。
腊月的天气时常阴得发绿。难得地遇到几个好太阳,母亲便匆匆拆被洗被,用浓浓的米汤把被子浆得硬邦邦的如同一面面大铜锣,让我们在漫长的冬夜充分享受着清新醉人的阳光气味。腊月,卤、炖、烧、炒、炸,灶台的使用率实在频繁,柴锅大灶与煤炉都要粉墨登场。这时候,我们便也十分地听话,在太阳下把煤球做得如同一枚枚黑色的弯月,横竖成行不亚于小字本方格中的汉字。劈柴也是一件很惬意的事,手起斧落,一劈两半。咔嚓咔嚓的碎裂声里,总是让我想起语文课本上“蓝鼻子哥哥与红鼻子弟弟”的故事来,汗水淋漓中一边欣赏着自己的劳动成果,一边慢慢地品味着劳动的幸福与乐趣。
当厚厚的积雪覆盖了小镇那黑色屋顶上的一棵棵瓦松,覆盖了街心光滑如镜的青石板,母亲开始用劈柴填进彤红的灶堂,炒花生果,炒玉米花,炒葵花籽儿,还有大人小孩都吃腻了,如今却堂而皇之地摆上超市柜台上的那种山芋角。瓷坛装满了,铁瓶装满了,剩下的,还有一屋子弥漫着的香气与欢乐。
母亲做完了这一切,一家人便开始翘首期盼,期盼远方的父亲踏雪归来。此时的年,就不仅仅是个隆重的节日,而是一种亲情的团聚,一种天伦之乐,一种传统与文明的写意。在商业部门工作的父亲这时总是忙得抽不开身,直到腊月三十的这天下午才披着一身雪花,一身疲倦,一身满足,步履蹒跚,哈着热气,笑盈盈地跨进大门。这时,大红的春联便被早早调好的浆糊平平整整地贴上所有的门窗户扇,通街最漂亮的杨柳青年画,一幅一幅齐刷刷地挤进了我家临街的厅堂。客厅的墙壁糊上了崭新的报纸,拉上飞翔的“和平鸽”,挂上一只只彩球和灯笼,点上最明亮的保险灯,端上热气腾腾的年夜饭,腊月的最后一天就在一阵阵喜庆的鞭炮声中,走进了一年的辉煌与极致。
(作者作品散见《重庆日报》等报刊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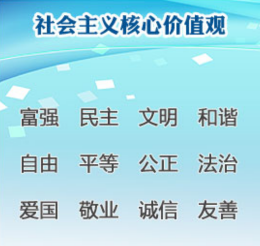
 渝公网安备50011202500163号
渝公网安备50011202500163号 