◎ 吴佳骏
那一日,去万盛。
那一日,去万盛王家坝。
时令已是初夏,天光亮得没有杂质。极目四望,万物生机勃发。有一种力,在天地间游走,我看不见它,却能感觉到。或许是受了这股力的牵引,不知不觉间,我乘坐的车便停在了王家坝的地盘上。
推开车门,便与阳光撞了个满怀。我抬头望天,白云依旧很白,蓝天依旧很蓝。有几只鸟雀,唱着歌从天幕上滑过,似在欢迎我,又似在对夏日发出私语。我不知道说什么好,唯心头涌起一股感动的潮水。
在城市里待长了,忽地来到这村野之地,我有一种想落泪的感觉。这绝非矫情,实因我的心被幽囚得太久,险些丧失对自然万物的敏感。试想,如果一个人活着,他的心却先死了,那将会怎样?不敢细想,细想是一包毒药,想得越深,毒性越大,直至身心都麻木,麻木到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尚活着。故许多时候,我都不想,不想过去和未来,不想白天和黑夜,不想晴天和雨天,不想土地和天空……遗憾的是,不想也是一种想,非想非非想。可见,人要挣脱自己想与不想的藩篱,何其难。不想吧,自己毕竟是一个人,不是一头猪或狗;想吧,终究会将自己想成非人的模样。
好在王家坝不会想我是想还是不想,它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,任天空的鸟飞远,任地上的人走近。街道上,只有我和我的影子,在互相追逐。这条街道不长,像季节的一条尾巴。如果快走,几分钟就能走完。但我走不快,每走一步,都似艰难的跨越。街道两边,屋舍俨然,独不见人。人去了哪里,估计连人自己都不清楚。只是街道的拐角处,有一个妇女,在弯腰洗头。长发盖住了她的面孔,也盖住了她的沧桑。妇女的旁侧,坐着一个老人,不说话,目光盯着眼前的一个瓷盅,仿佛那个瓷盅里装着她的青春、记忆和荣辱。
我也不说话,我是王家坝地底的一块煤,只酝酿属于我的火焰。但我的火焰仅能照亮我自身,更多的煤,则走失在酝酿和寻找火焰的路上。那些即使没有走失的煤,也早已成为王家坝的记忆标本,或一个年代的物证。
抓住记忆的辫子,我从街道上转身,爬上通杆坡。在不需要火光的年月,我喜欢站在高处,去努力接近星辰。坡巅生长着一棵上千年的黄葛树,树冠延伸向整个坡沿。远远看去,宛如岁月女神撑开的一把绿色巨伞。若干年前,这树下有一条古道,往来的行人牵着马,马驮着茶叶,与生活做着交易。也许,这棵树就是当年的某个商人栽种的。他想以这棵树来铭记什么,昭示什么,象征什么。然而,时序更迭,斗转星移,当年植下这棵树的人今安在?看着这棵树慢慢长大的人今安在?在这棵树下乘过凉的人今安在?树肯定知道答案,可树不说。树之上的太阳、月亮和星星也知道答案,可它们更不说。不说是对的,哪怕能说出时间的历史,也无法说出人的心路历程。
黄葛树周围,种满了桃子和金丝皇菊。我绕着田野走了一圈,错过了花期,没有错过果期。我摘下一个桃子,咬了一口,满嘴果香,好似吃了一口治疗乡愁的药。那些金丝皇菊呢,还不到出嫁的时候,自然也就没有将自己开成一朵花中的皇后。
我找了块石头坐下来,等花盛开,等时光老去,等另一个自己,从初夏款款走来。
(作者系青年散文家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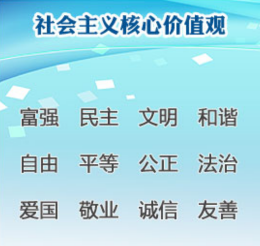
 渝公网安备50011202500163号
渝公网安备50011202500163号 