◎ 李享奇
小满那天,虽有雨,但天亮雾稀,风中弥漫着黄桷兰的香气。路上遇到很多喜庆的婚礼车队亮着双闪车灯驶过,一定是个良辰吉日。
我和父亲共撑一把雨伞,并肩前行,去见他多年未见的发小。这个世界有时很大——父亲甘肃老家的小伙伴,读书求学走出大山,为了生活各奔东西,多年难见一面;这世界有时又很小——十二年前,我和父亲发小的孩子都到重庆就业,而且都在基层派出所工作。这天也是父亲发小女儿大婚的日子,父亲顺道来看我,邀我一同前去吃喜酒。
父子难得相聚,我俩聊着天,走呀走,不知不觉走了五里地。父亲是一位退休乡村老师,岁月不饶人,花白的头发和一双粉笔腐蚀摧残裂开的大手,在雨伞下更加显眼。雨一直在下,气氛却非常融洽,肩并肩挨着的一面都是干的,外侧衣袖被淋湿了。父亲打伞时顾及我,我打伞时要照顾他,唯一的一把雨伞在我俩头顶来回移动。
久别重逢,父亲和发小互相叫着小名,手拉手畅聊了三个小时。从小时候捉鱼摸虾聊到现在练习太极,再从曾经一起获得“三好学生”荣誉聊到上年龄患了“三高”疾病,他俩难舍难分。席间,我给父亲夹了一块三文鱼,他说,这是他第一次吃三文鱼,吃不习惯。这些年不在父母身边,心里难免感到亏欠和内疚。
婚宴结束,父亲要回去了,我送他到火车北站南广场的汽车站。受疫情影响,没有比肩接踵的场面,人少车也少,一点都没有火车站和汽车站周边的热场面,大周末,冷清得连标配的小贩和卖稀饭凉面的小摊都看不到。
车站出入口“戒备”森严,不是体温枪测一测,就是二维码扫一扫、验一验,防疫措施非常严格。第一道关卡:出示渝康码。父亲慌乱地关闭常用的陇康码,又翻找渝康码,居然还打开微信里的支付码;第二道关卡:出示行程码。父亲勾选着手机里接二连三的同意或选择选项对话框,收到验证码后,又找不到信息了,点了“返回”后点“打开”,按了“打开”后再按“返回”,他使劲戳着屏幕翻找,复制粘贴也甚是费力,好不容易才展示出绿色通行的箭头标识;他脸上刚露出轻松的微笑,谁知又来到第三道关卡:扫场所码。这是父亲第一次遇到,发现他不会使用,两位热心的安检人员欲上去帮他,我致谢后拒绝了。我说:“我们不赶时间,让我爸多练习一下,以防我不能陪伴的时候,他能不求人了。”这一切并不轻松,通过他自己的努力,花了很久时间才通过“三关”进入候车大厅。
当手提包缓缓过安检扫描仪,我的思绪也随着时光通道回到了过去。
那一年夏天,离开生我养我的村庄,一路北上赴河北保定上大学。临行前,父亲给我一张火车票,嘱咐了很多话:“到就近的略阳火车站乘车要小心谨慎些,不要轻易和陌生人说话,牢记车次和站台,千万不能坐错火车,我让你母亲在内衣内裤里面隐蔽的位置缝制了夹层小包,可以藏钱和银行卡;当然不要担心丢失,也不用时刻摸它,钱财都不重要,保护好自己才重要。”和朱自清的父亲一样,分别的时候,他虽有万分的不舍,却云淡风轻地说:“放心大胆去吧,以后的路就靠你自己了,去吧,到学校来信!”
那时的父亲多么强壮,多么年轻!帮我扛被褥,还拖拽着行李箱,他好像什么都知道,火车会经过哪些地方、怎么在火车餐厅吃饭……他介绍个不停。我安静听他说着,只知道点头回应,心早就跑远了。我从未离开过大山,更没有出远门的经历,对外面的一切充满好奇,连车站小卖部里花花绿绿的饮料瓶子都觉得无比新鲜。但那时的我,一切都会谨遵父亲教诲,他的指示就是最高指示,他的话就是世界上最安全、最可信、最踏实的话。
“旅客朋友们,排队取票时请戴好口罩,保持间隔距离一米……”传来的广播声音打断了我的回忆。此时此刻,城市偌大的车站里,空旷无比,像一个偏僻地区的小镇车站一样孤独。就在父亲眯着眼睛靠近取票机屏幕,艰难地阅读网络购票信息时,我发现,父亲老了。
(作者单位: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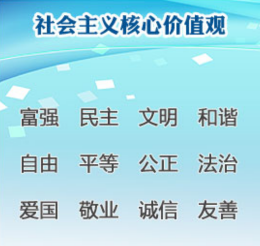
 渝公网安备50011202500163号
渝公网安备50011202500163号 